
动身去南美丛林之前,我在巴黎的实验室里精心准备了一副皮绑腿,以防在丛林里遭毒蛇咬;在右绑腿的外侧,还配上一个大学时代的同窗赠送我的蒙古刀,或许它在我与野兽搏斗之际会派上用场。不知别人的感觉如何,我当时是自以为有点美国西部牛仔的味道。
进入丛林,自然不肯将绑腿闲置起来。第一天随一个法国年轻人在雨林里转了一圈,第二天便开始一个人“闯荡”了。说实话,独自进南美丛林,真有点忐忑不安;但想起中国即来之则安之的古话,胆子便一下子壮了。沿着森林中被人踩出的小路慢慢向前走,东瞧瞧西望望,到处是高高矮矮的藤和树,形形色色的花和果,不知不觉中,竞早已忘记了最初的恐惧。偶尔,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两声清脆的鸟鸣,使雨林更显得神奇莫测。小路蜿蜒持续到离河边不远处的陡坡,没有伸进河里却沿着河流的方向拐了个弯,但路与河之间也只隔着一片齐膝深的草。探头仔细瞅瞅,河水不深,清澈见底,还依稀可见半尺长的热带鱼在水中缓缓地游来游去。激情在一瞬间泛起,这下子可以痛痛快快地洗个冷水澡了!什么都没再多想,我拔腿进了草丛。一步,两步,刚迈出第三步,隐约感觉一个棍状物在急促地敲击左侧的小腿。我收住脚,轻轻拨开草丛,天啊!竟是一条后背布满斜方格纹的暗褐色的蛇,它有一米半长,尾巴高高地翘着,左右摆动,正打在皮绑腿上。蛇的头也高昂着向后扭曲,似乎在盯视我的一举一动。我一下子“懵”了,心想:完了,这家伙非“给”我一口不可。我呆呆地站着,任凭时间悄悄划过;想抽出腿上的刀,却怕因此惹怒对手而闹个两败俱伤。蛇也保持僵硬的姿势,似乎没有向我进攻的意思。我定了定神,觉得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便稳住心绪,缓缓地将左腿“拔”出来,慢慢放在右腿的后边,然后再悄悄拔出右腿。一步,两步,我一口气退回到离蛇十几米远的地方。这是在雨林中与蛇的第一次遭遇,或许还真是皮绑腿帮了我的忙。
逐渐地,见的蛇多了,便学会了如何鉴别有毒蛇与无毒蛇,对蛇不再恐惧,也不再使用皮绑腿。其实,有毒蛇与无毒蛇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主要分两大类:蝰科和眼镜蛇科。蝰科蛇头部呈膨大的三角形,尾部骤然变细;眼镜蛇身体一般有环纹。不过,更精确的外形分类标准还在于它们体表的鳞片结构和形状,蛇一生中可以多次蜕皮和变换体色,但其鳞片结构是一成不变的。再后来,竞不知不觉地喜欢上蛇,也开始“玩”蛇了。生态站有规定,为了鉴定和研究的需要,可以捕捉动物,但必须在尽短的时间内将动物送回“原籍”。当然,也有蛇主动前来登门拜访。某天早晨,有人在鞋里发现了黄色小蟒,它刚刚吞食一只绿色大鸟,肚皮撑的成了半透明,跑到鞋里消化来了。某个暴雨倾盆的下午,一只巨大的青蛙在帐篷旁边发疯般地向前蹿,我探头一看,好家伙!原来是3米多长的棕黑猎蛇尾追其后。不过,更滑稽的还得数下面这个插曲:
玛迪妮是个小个子法国女学者,到生态站研究一种形体很小的负鼠。为了科学研究,她需要捕捉两只动物带回实验室。这种负鼠习夜行性树栖生活,所以必须将捕捉动物的笼子吊挂在20米高的树枝上才可能奏效。玛迪妮个头小,力气也小,每天将十几个笼子吊上吊下地换诱饵,对她来说真不是件容易事儿。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花了一周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终于捕到了两只“宝贝”。“宠物”被关在网眼不大的精致的笼子里,放在高高的桌子上。怕它们夜里饿着,傍晚还特意多加了两个熟透了的香蕉。可第二天一早,“奇迹”发生了,两只负鼠竞在一夜之间“变”成两只肚子鼓鼓的假金环蛇。原来,不知是这对蛇恰好打此路过还是被关在笼子里的负鼠吸引到这里,蛇顺着笼子的网眼钻了进去,吞食了负鼠,却因身体变粗而无法再钻出来。
记忆最深刻的一次“玩”蛇是与蟒的较量。一个傍晚,我正在吊床里整理观察数据,猛听见邻近帐篷里两个“撒拉马干”人的变了音调的惊叫声。不用猜便知道,一定又有蛇前去“光顾”了。说来也怪,土著人可以镇定自若地面对凶悍的美洲豹或者一群几百只的野猪,却单单对蛇,哪怕最小的无毒蛇也惧怕得要命。我急忙爬起来帮他们“解围”。过去一看,嘿!难怪他哥俩比以往喊叫得更令人毛骨悚然,一条小蟒蛇竞大摇大摆地横在他们门前。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蟒,但我根据书中照片留下的印象一眼就认出这是“空中彩虹”,它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名字是因为蟒蛇的棕色身躯在日光下闪烁着金属光泽,其体表还嵌着大大小小的暗黑色圆环,正仿佛雨后的彩虹。搏斗的兴致霎时被这美丽的爬虫激起,我取了根适手的棍子,试图按“传统”的方法将棍子压住蟒的头颈,然后紧抓它的后颈以免它攻击。谁知这一次竞不奏效,“空中彩虹”头颈和身体剧烈地扭曲,顶着棍子的压力快速蠕动。我不能用力过猛,怕伤着这“稀客”,又不敢贸然去抓,眼瞧着蟒蛇钻入木板下的空隙中。这下子麻烦大了,如果不把蟒蛇搞出来,两个撒拉马干朋友是绝不敢进帐篷睡大觉的。
我想一个好办法,取出平时捉蝴蝶用的网;别的同事在另一侧连敲带推,使出浑身解数将蟒蛇逼了出来。我守株待兔地将网支好,蟒蛇缓缓地钻了进去。可惜网太浅,蟒蛇的头部已经触到网底,身体却还有三分之一留在网口外。更出乎意料的是,蟒蛇可能意识到被围困,猛烈地向前闯,竞把网底撞开一个洞。我不敢再怠慢,伸出左手一把抓住蟒的脖子。蟒蛇也急了,头和颈猛烈摇摆想从我手中挣脱,身体也扭来扭去试图缠卷我的手臂和身体。我连忙用右手化解蟒蛇的一个个招数,避免被缠住。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空中彩虹被降服了。一点点将它从网中取出,两手托着几公斤重的蟒,我兴奋极了。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站里的同事都希望第二天能同空中彩虹合个影,我只好让它在封闭的桶里委屈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将蟒蛇“放生”在离“撒拉马干”帐篷较远的空地上。蟒蛇出来的瞬间,大家都以为它会飞也似地逃遁,做好抢拍的准备。谁知空中彩虹竞耍起倔来,身体盘卷着,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动也不动。几个女孩子开心地上前“抚摸”这乖巧和温柔的爬行动物。谁知,逐渐地,蟒蛇失去了耐性,猛地探出头,身体开始蠕动,紧接着全身扭曲。我急忙跑到蟒蛇前方,试图阻止它一下子逃进森林,这一次空中彩虹发怒了,昂起头唰地扑向我,我急忙躲闪,乖乖地看着它消失在森林里。
不过也有玩蛇玩“砸”了的,生态站曾因此闹过一次恐慌。那是一个傍晚,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实习生马克在森林旁边发现了一条小蛇,便用皮手套将它裹回来。荷兰女动物学者玛嘉在昏暗的灯光下冒冒失失地伸手抓蛇的颈部,谁知没捏住,蛇扭头咬了她的食指。再仔细一辨认,竟是一条剧毒的珊瑚蛇,生态站的空气骤然间紧张起来。不出所料,一会儿的功夫,玛嘉手臂开始麻木。大家慌忙翻出储备的蛇药,不料蛇药竞早已过期失效。再通过无线电与100公里以外的机场取得联系,直升飞机也因夜幕降临而无法进入森林。生态站的空气凝固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玛嘉昏昏欲睡,这正是眼镜蛇科蛇毒的发病症状,这类毒素的作用方式是神经性的,导致被咬者中枢神经系统麻痹而死亡。我们费了不少周折终于和位于卡宴的急救中心通上了无线电话,根据医生的吩咐,大家在整个晚上轮流看护着她,阻止她入睡。终于,漫漫长夜挨过去了。庆幸的是这蛇还小,又只咬破了手指尖的皮肤,中毒不深,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照片提供:澳门赌场动物研究所网络信息中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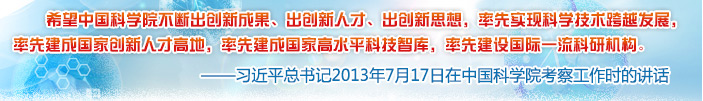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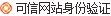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